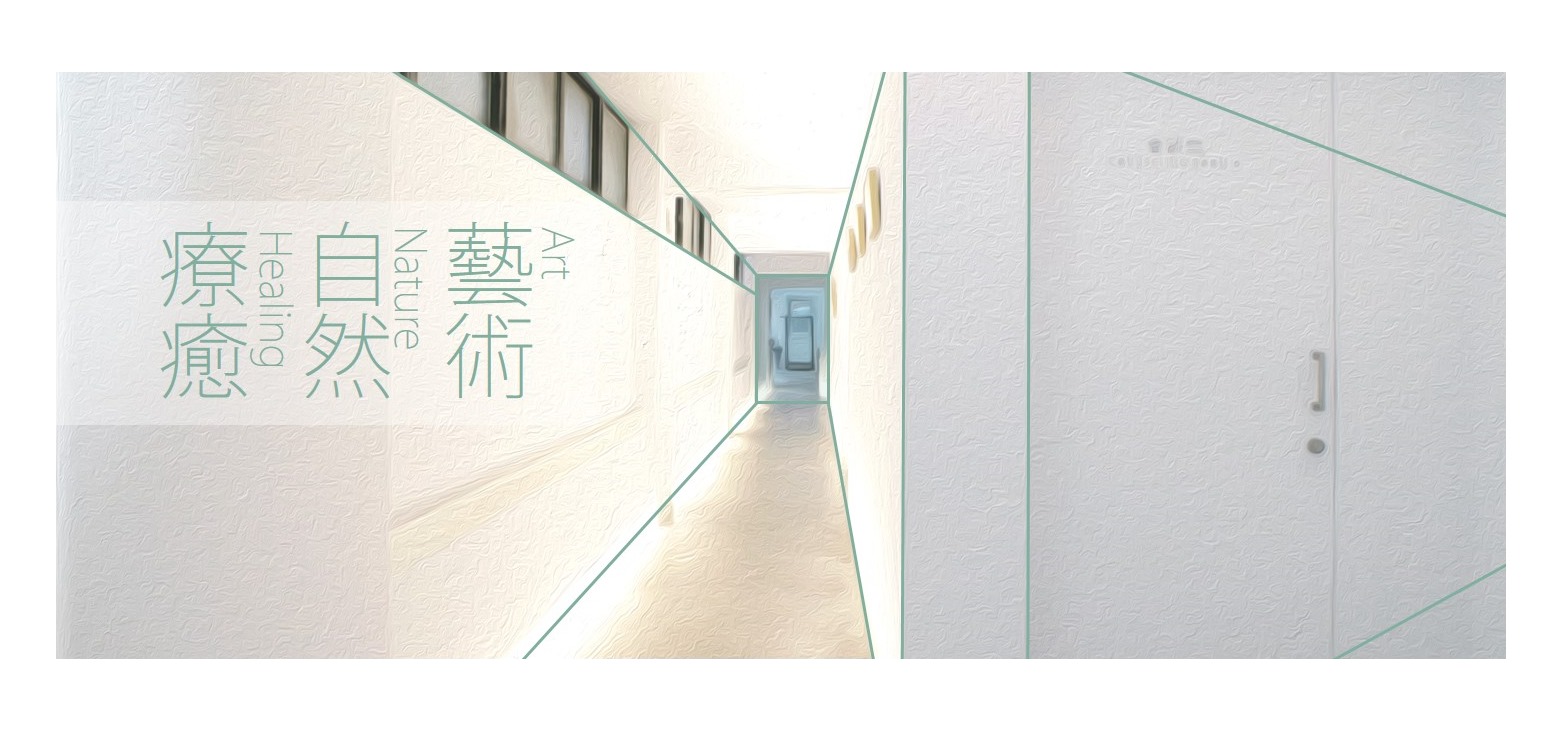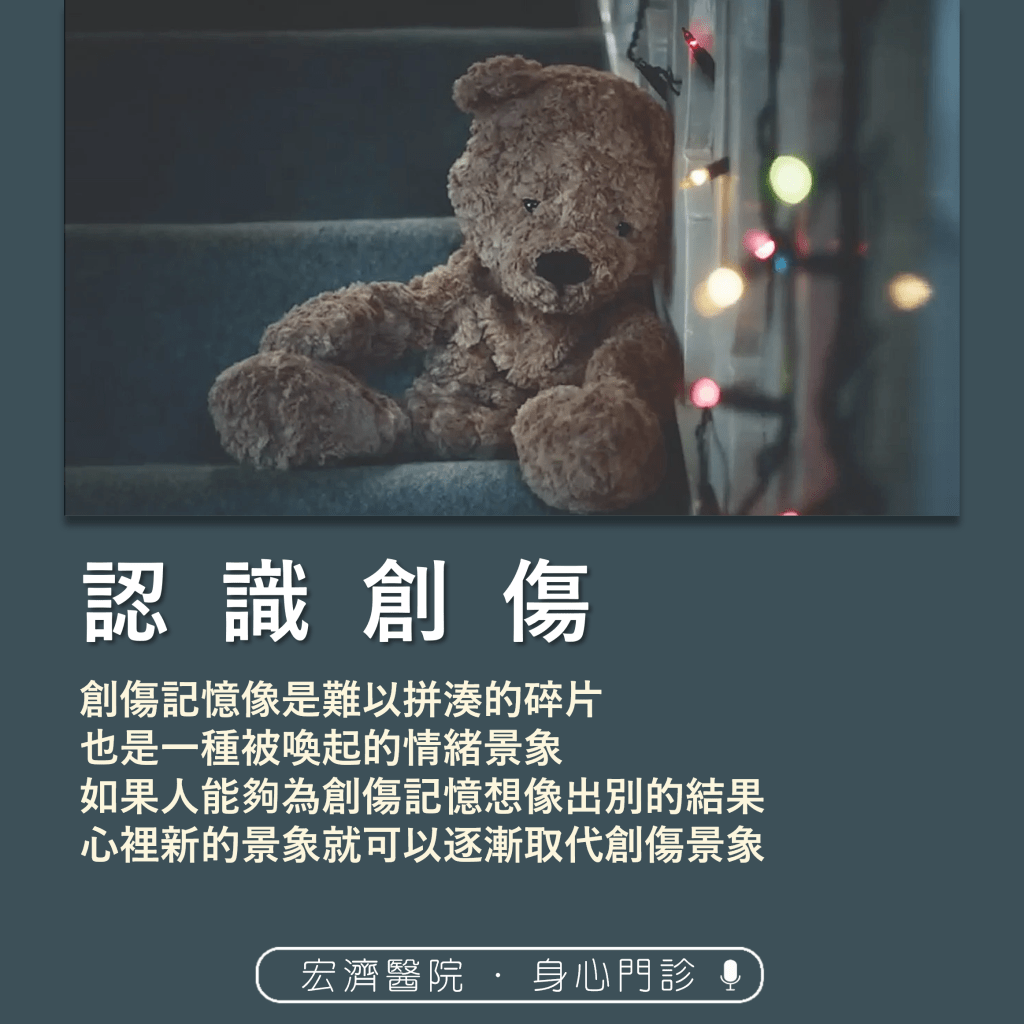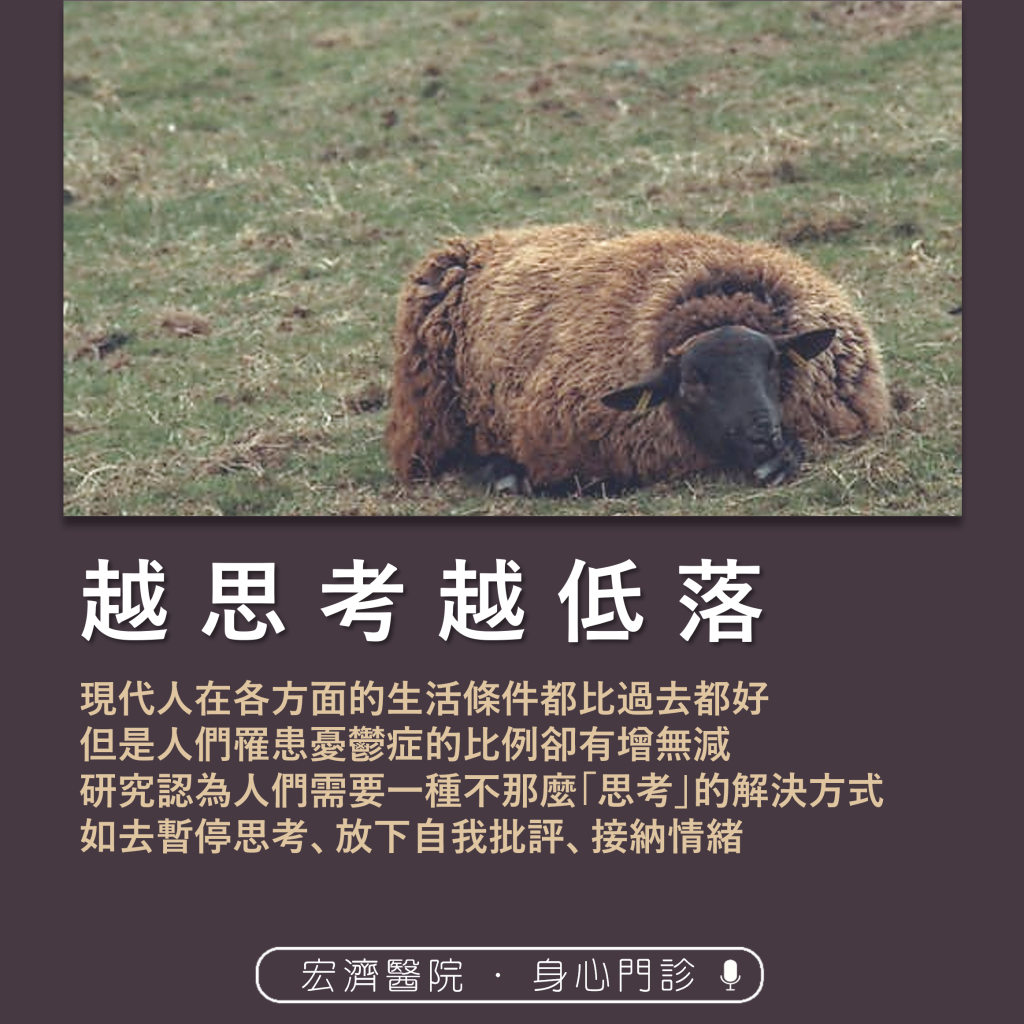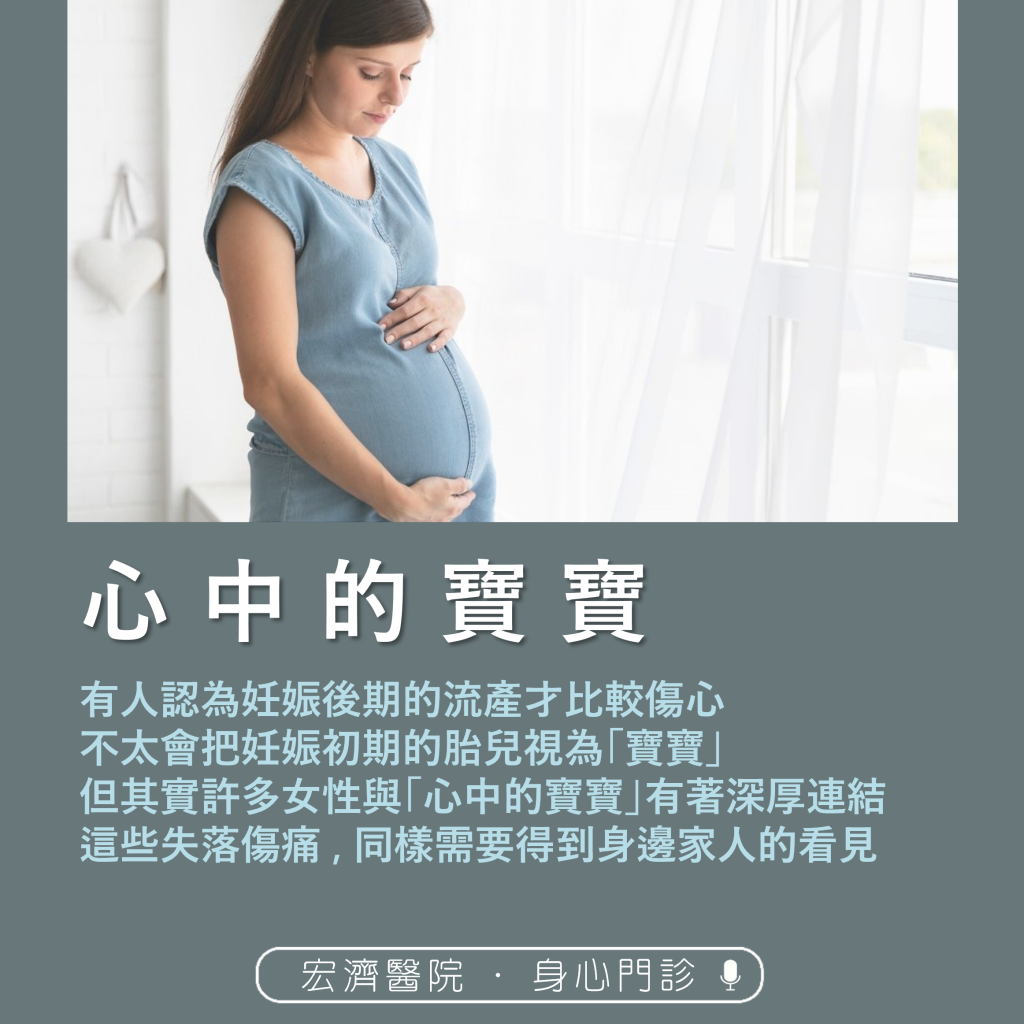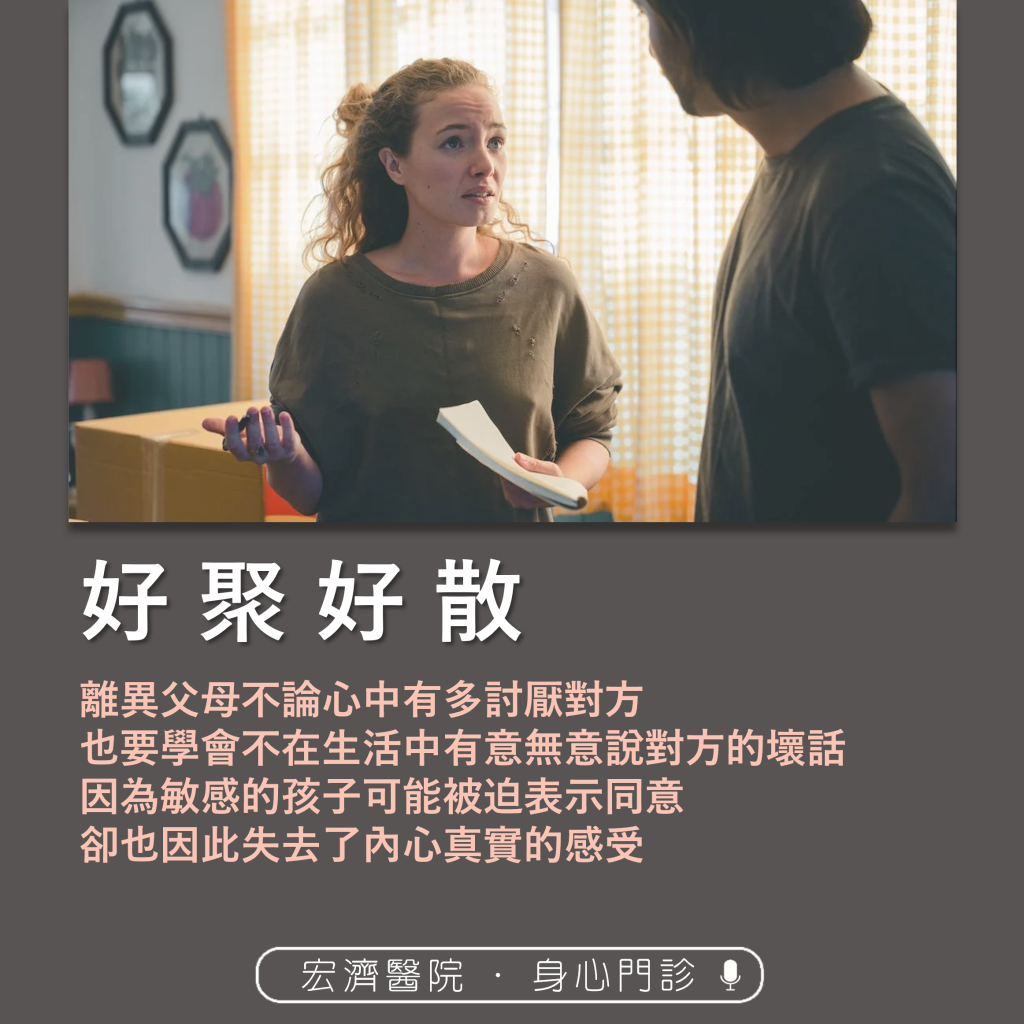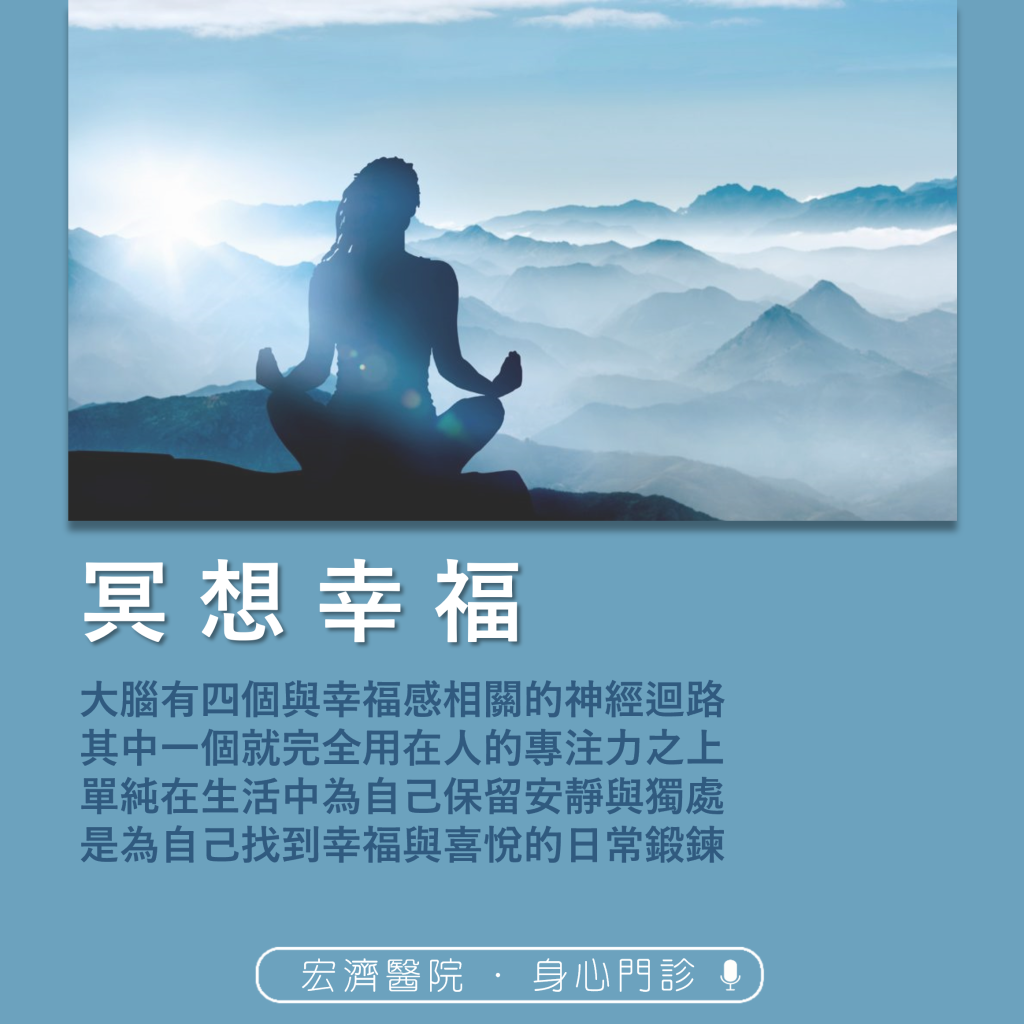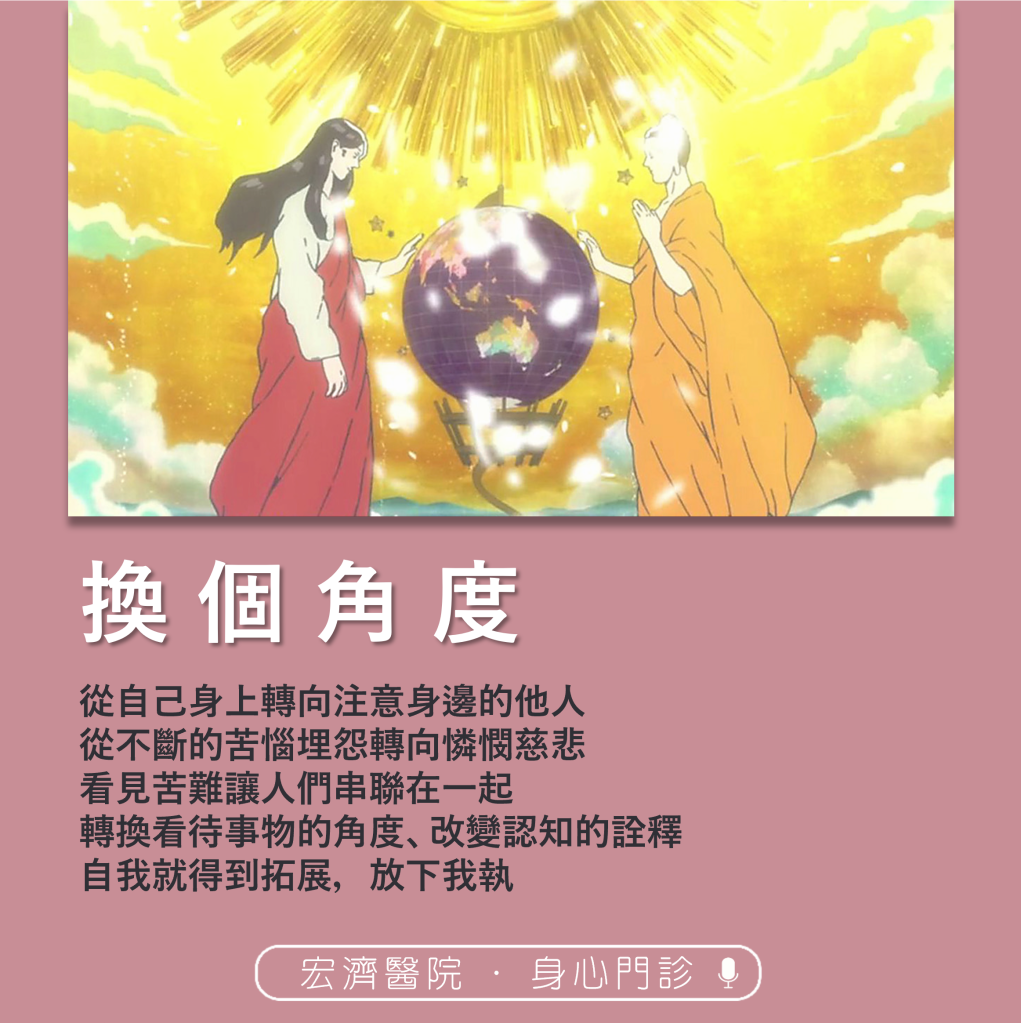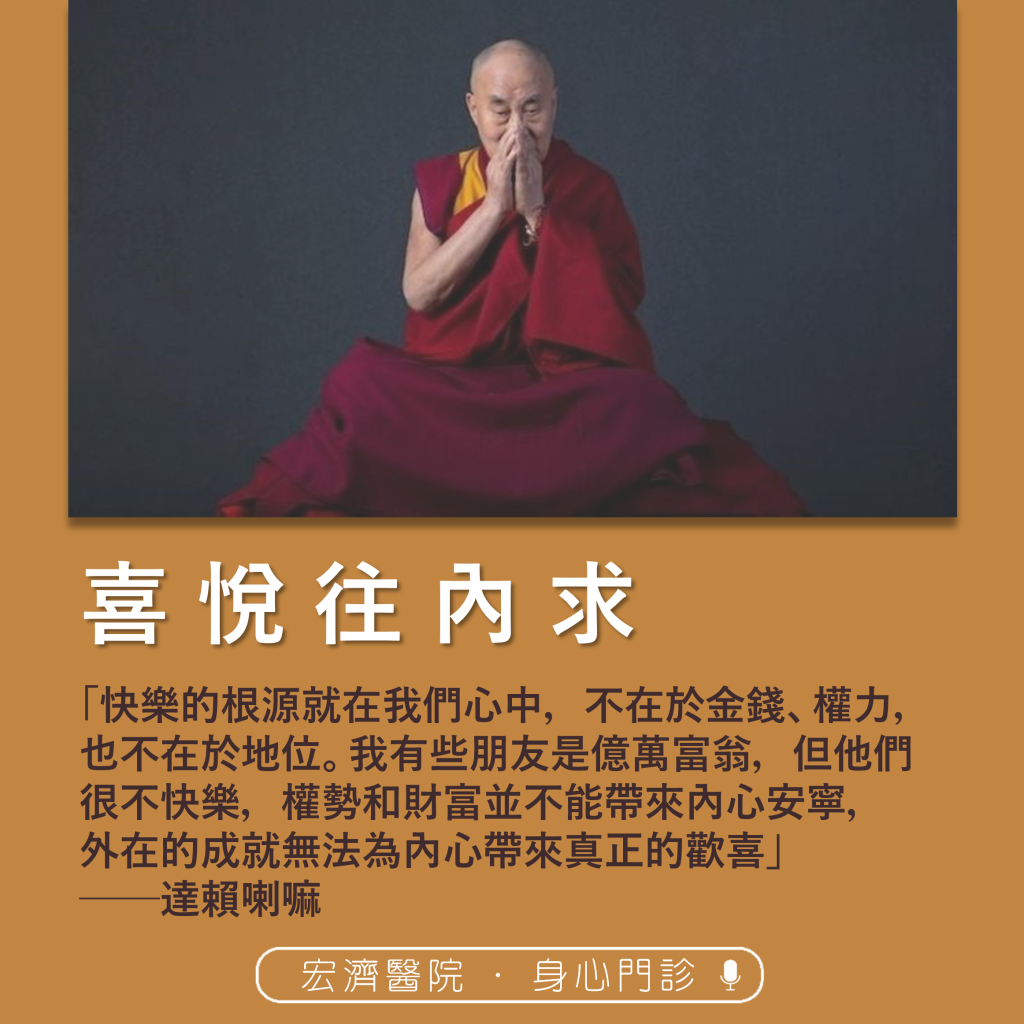文字:本院 蘇俊濠 諮商心理師
童年逆境經驗(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)是留存於體內的毒性壓力,它存在於非語言的右腦,干擾安全依附。許多時候,人們就算沒有受到甚麼外界困擾,也可能在一個人的晚上突然感到一陣悲傷難過,這可能代表著潛意識的創傷在暗地發作。
調節與控管壓力,幾乎是都市人每天都需要的自我療癒任務。童年毒性壓力與創傷發作時,大腦的思維和語言區域活性(即理性與思考能力)會開始下降,人們變得很難再依靠邏輯和語言來自我幫助。一開始,人們處於過度警覺和情緒化的「過度喚起狀態」,然而當承受壓力過久,人就會被壓垮,最終陷入麻木、癱瘓與崩潰的「過低喚起狀態」。
為能夠讓自己再次理性地思考和有效自我調節,回到壓力不過高也不過低的「彈性狀態」,我們需要基於身體本能、讓大腦各區塊重新上線工作、恢復身心聯繫感的技巧與練習。好比壓力來臨時,我們未必得思考發生了甚麼事,而是改為「追蹤」(Tracking)身體發生的事,只集中去感知身體的知覺,其實就能安穩情緒。
我們可以嘗試下面四個技巧:
(1)揉捏身體:將一隻手放在另一隻的手腕上,深深感受皮膚被揉捏、施壓、放鬆的感覺,過程中可以調擠壓的速度、深淺、角度、方向等,作多元的感受。
(2)體察身體:把手放在胸前、腰間或肋骨旁,呼吸時深深感受手掌有著怎樣的觸覺變化,那些體內的膨漲與收縮、溫和與放鬆、起伏跳動。
(3)移動身體:由於壓力反應會讓人想要行動(戰/逃),所以我們可順應本能,移動身體來釋放這些肌肉裡頭的張力,如去深深感受伸展手臂或推一面牆的感覺。
(4)改變身體:童年毒性壓力會讓人習慣彎腰弓背,所以當壓力再臨時,就會傾向喚起同樣的肌肉姿勢,因此反其道而行,試著抬頭挺胸坐直來扭轉身體感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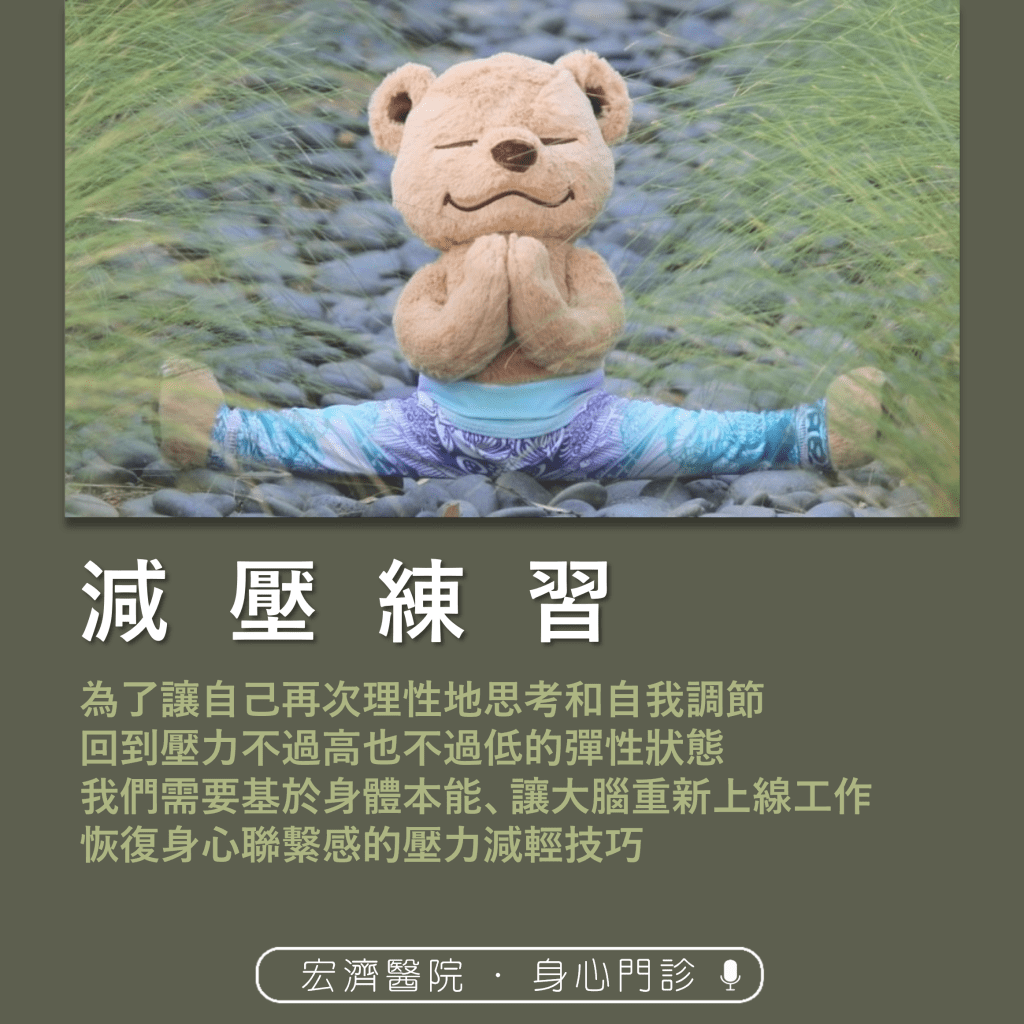
各種「正念冥想」的方法,都主要透過專注於身體感受,而非試圖改變或評價它,好用全然的好奇去回復身心平靜。面對情緒感受,要學會放下「這感受太糟,我無法忍受!」的想法,而改為「這只是感覺,我感受一下,而且感覺並不是我的本質!」的態度,用非責備或非挑剔的方式來重建受長壓力壓跨的自尊。
「自我慈悲」練習能有效回應情緒,我們可以默唸與承認:
承認我們正在遭受痛苦 → 承認每個人有時都會受苦 → 此刻我可以自我慈悲。
接下來,試著每週、每天的進行練習:
(1)找一個二十分鐘內都不會被打擾的地方,把雙腳平放在地板、坐直、但肌肉要放鬆。閉不閉眼都可以,試想像身體像雄偉的山,不論陰晴都能穩坐,在身體的呼吸中休息。
(2)留意呼吸,在呼吸時感受體內的情況,感受腹部、肋骨、胸部、心跳、鼻子等,好奇地觀察各身體部位在呼吸時有著怎樣的感覺。若腦袋有一些想法冒出來拉走注意力,就耐心地、輕柔地把想法和注意力都送回至呼吸的節奏裡頭。
(3)回想最近令自己稍微不安的情況,這可能是工作或家庭上感到的拒絕或憤怒,讓自己保留關注但不評判這些情緒感受,在這樣的空間裡留意身體哪個部位會因此有所不適。
(4)在身體承受不適的地方吸進慈愛,想像自己被慈悲的力量包圍、去抱住內在小孩,直到小孩停止哭泣,並開始重新去玩耍。
(5)把一隻手輕輕放在承受不適的身體部位上,想像自己是慈愛的父母般珍重著自己。專注呼吸,直到慈悲充滿身心,舒緩下來,說出「我要快樂、我要安心、我要完整」。
參考:《背負創傷長大的你,現在還好嗎?》(幸福文化出版)